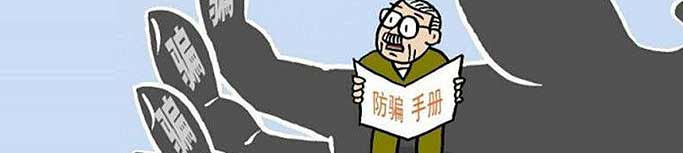首頁(yè) >> 正文
|
|
|
作者:厲以寧 |
厲教授認(rèn)為,從1979 年起,,中國(guó)進(jìn)入了“體制轉(zhuǎn)型和發(fā)展轉(zhuǎn)型”的雙重轉(zhuǎn)型階段,,從計(jì)劃經(jīng)濟(jì)體制轉(zhuǎn)向市場(chǎng)經(jīng)濟(jì)體制,傳統(tǒng)的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轉(zhuǎn)向工業(yè)社會(huì),?!皟煞N轉(zhuǎn)型的結(jié)合或重疊,是沒(méi)有前例的”,,當(dāng)中積累的經(jīng)驗(yàn)包括:要以體制轉(zhuǎn)型帶動(dòng)發(fā)展轉(zhuǎn)型,;解放思想,清除計(jì)劃經(jīng)濟(jì)理論的影響,;把產(chǎn)權(quán)問(wèn)題放在改革的首位,;在經(jīng)濟(jì)增長(zhǎng)的同時(shí)改善民生;不斷提高企業(yè)的競(jìng)爭(zhēng)力,,核心是鼓勵(lì)自主創(chuàng)新,;重視經(jīng)濟(jì)和社會(huì)的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問(wèn)題;通過(guò)提高城鎮(zhèn)化率繼續(xù)助推實(shí)現(xiàn)雙重轉(zhuǎn)型,;大力發(fā)展民營(yíng)經(jīng)濟(jì)以緩解就業(yè)壓力,,調(diào)動(dòng)民間的積極性和民間資本的潛力。
從表面上看,,厲教授這些娓娓道來(lái)的大白話(huà)和大實(shí)話(huà)似乎無(wú)甚高論,。但我們不要忘記,我們之所以覺(jué)得稀松平常,,恰恰是因?yàn)檫@些主張是在過(guò)去數(shù)十年實(shí)踐的基礎(chǔ)上得以提出,、補(bǔ)充、修訂,,并最終深化與上升為理論,??梢哉f(shuō),厲教授這本《大變局與新動(dòng)力》的前半部分,,揭示的恰恰是從嘗試到常識(shí),、從具體進(jìn)入抽象的過(guò)程,也就是我們習(xí)以為常的“共同知識(shí)”的形成過(guò)程,;而這本書(shū)的后半部分所重申與強(qiáng)調(diào)的關(guān)鍵與重點(diǎn),,則是從常識(shí)到重拾、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(guò)程,,也就是面對(duì)新問(wèn)題,、尋找新動(dòng)力、構(gòu)建新理論的過(guò)程,。
目前,,我們面臨著經(jīng)濟(jì)增速放慢乃至遇到下行壓力的“新常態(tài)”。厲教授認(rèn)為,,“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到一定階段,,原有發(fā)展方式的不足之處就會(huì)相繼反映出來(lái),這就是紅利喪失的主要原因”,。但所有紅利都依賴(lài)于我們“從無(wú)到有”或“推陳出新”的創(chuàng)造,。在國(guó)企改革、城鎮(zhèn)化改革,、財(cái)稅改革和社會(huì)治理體制改革者四大領(lǐng)域的改革之外,,厲教授提出,我們應(yīng)當(dāng)用新體制,、新機(jī)制的制度環(huán)境,,用群眾和企業(yè)的活力,用創(chuàng)意,、創(chuàng)新,、創(chuàng)業(yè)和競(jìng)爭(zhēng),去努力保護(hù)和促成新紅利的涌現(xiàn),,包括新人口紅利,、新科技紅利等在內(nèi)的新資源紅利,以及包括社會(huì)和諧紅利在內(nèi)的新改革紅利,。只要不停地有新紅利涌現(xiàn),,就不必?fù)?dān)心經(jīng)濟(jì)停滯和社會(huì)衰退,而且“各種紅利一直是相互聯(lián)系的,,它們作為改革的成果,,可能相互啟發(fā),相互促進(jìn)”,。
“思想解放和理論創(chuàng)新都沒(méi)有終點(diǎn),,也不可能有終點(diǎn)”,。實(shí)踐要求研究者不斷學(xué)習(xí)、成長(zhǎng),、提高,,也要求理論不斷修正、豐富與完善,。在“市場(chǎng)的道德與效率”一章中,,我們可以看到厲教授更為深入的探索與反思,。
厲教授指出,,在傳統(tǒng)的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思想與方法的指引下,“效率標(biāo)準(zhǔn)是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的標(biāo)準(zhǔn),,效率判斷也是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中的判斷,,而道德標(biāo)準(zhǔn)和道德判斷都不是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的研究對(duì)象或研究任務(wù)”“通常只著重經(jīng)濟(jì)因素與技術(shù)因素,而忽略非經(jīng)濟(jì)因素與非技術(shù)因素,;只在意利益的影響,,而不注意社會(huì)責(zé)任感與公共目標(biāo)的作用;只強(qiáng)調(diào)物的價(jià)值實(shí)現(xiàn),,而忽視人的價(jià)值實(shí)現(xiàn)”,。厲教授進(jìn)一步闡述,要想提高效率,,發(fā)揮潛力,,就要正視、尊重和倚重效率的道德基礎(chǔ),,“一要靠對(duì)人的自主性的尊重,,以便人的積極性、創(chuàng)造性能得到發(fā)揮,,二要靠人際關(guān)系的協(xié)調(diào),,靠人同團(tuán)體、組織,、社會(huì)的適應(yīng)”,。
厲教授認(rèn)為,改革的“攔路虎”包括利益集團(tuán)的干擾,、制度慣性的存在,、完善與獨(dú)立的市場(chǎng)主體的缺乏,要深化改革還必須重視信用體系的建立和道德力量的調(diào)節(jié),。事實(shí)上,,厲教授的這一主張可以進(jìn)一步引申開(kāi)去,那就是:個(gè)人,、社會(huì)與政府都要講求信用,,都要受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調(diào)節(jié),。唯有如此,我們才有可能在大變局下實(shí)現(xiàn)厲教授所指出的他律和自律并重,、法律與道德的并重,、經(jīng)濟(jì)與文化并重,鍛造厲教授所期盼的動(dòng)力,、信念,、精神,造就厲教授所重視的“有道德,、有信念,、有信仰的個(gè)體”,最終獲得厲教授所強(qiáng)調(diào)的“新改革紅利”尤其是“社會(huì)和諧紅利”,。
市場(chǎng)經(jīng)濟(jì)并不必然伴隨著錢(qián)權(quán)交易,、尋租和腐敗等丑惡,也不必然帶來(lái)理想,、完美,、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。但市場(chǎng)經(jīng)濟(jì)無(wú)疑比平均主義更利于效率和發(fā)展,,又比單靠權(quán)力來(lái)分配資源和收入的方式更公平,。從這個(gè)意義上說(shuō),以?xún)r(jià)格改革或企業(yè)改革為主線(xiàn),、“激進(jìn)”或“漸進(jìn)”,、“市場(chǎng)”或“股份”、宏觀體制或微觀基礎(chǔ)等等之間的分野,,或許并沒(méi)有我們想象中那么涇渭分明,。恰恰相反,任何一位有社會(huì)情懷,、有公義良知的學(xué)者,,都應(yīng)當(dāng)保持自己對(duì)真實(shí)世界與重大學(xué)術(shù)問(wèn)題的敏銳體察和解釋力,都應(yīng)當(dāng)相信市場(chǎng)的分工,、競(jìng)爭(zhēng)與合作的巨大力量,,都應(yīng)當(dāng)牢記每個(gè)個(gè)體都絕不是無(wú)足輕重的數(shù)字,都應(yīng)當(dāng)避免只看效率,、只談產(chǎn)出的庸俗的形而下,,都應(yīng)當(dāng)警惕與抵制某些從“管治一切”變?yōu)椤肮苤埔磺小钡牟块T(mén)本位思維。
薩繆爾森曾經(jīng)說(shuō)過(guò),,要讓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“帶有一顆溫暖的心”,。我們期盼更多像厲教授在本書(shū)中所著手構(gòu)建的“有溫度的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”。這種以人為本的原則與情懷,這種對(duì)中國(guó)經(jīng)濟(jì)實(shí)踐具有超強(qiáng)解釋力和科學(xué)指導(dǎo)力的概念,、規(guī)律,、范式結(jié)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經(jīng)濟(jì)理論和分析框架,這種思想解放,、理論創(chuàng)新,、經(jīng)濟(jì)改革之間的良性互動(dòng),才是“中國(guó)特色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”以及中國(guó)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界真正的道路自信,、理論自信,、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所在。
(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博士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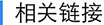

|
大數(shù)據(jù)提升中國(guó)人工智能“比較優(yōu)勢(shì)”

我國(guó)應(yīng)加快培育對(duì)外核心競(jìng)爭(zhēng)力,,加速人工智能產(chǎn)業(yè)對(duì)國(guó)外實(shí)現(xiàn)“換道超車(chē)”,。
 ?
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