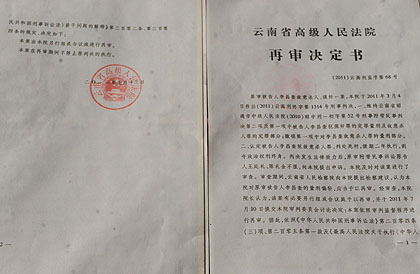相關(guān)報道:李昌奎案:輿論與司法的沖突讓人困惑
社會轉(zhuǎn)型時期,,各種矛盾紛繁復(fù)雜,處在此種社會背景下的刑事司法,,尤其是涉及到死刑適用的司法判決,,更是容易成為焦點。在這之中,,司法與民意的鴻溝究竟是如何產(chǎn)生的,,對司法權(quán)威與公信力會帶來什么影響,,它們又會在推動社會法治觀念進步上留下什么,值得我們深入反思,。
云南高院與“民意”抗?fàn)幍募ち页潭�,,是以往司法機關(guān)所罕見的。
7月的云南高院,,正陷入一場空前的輿情危機。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,,法院不得不對引起“民憤”的李昌奎案決定重審,。緊接著昭通再度爆出同類案件,因27刀刺死女孩而被一審判處死刑的賽銳,,也是被云南高院改判死緩,。不難想象,李昌奎案的再審結(jié)果,,已不單局限于個案意義,,更帶來深層面的司法影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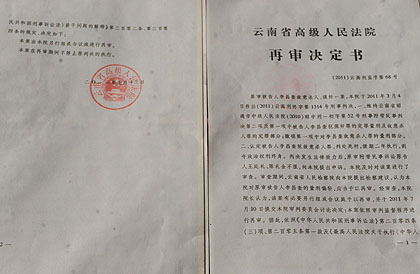
7月13日,,云南省高院啟動李昌奎案再審程序,,再審決定書已送達(dá)受害者家屬。圖為《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決定書》,。新華社記者
陳海寧 攝 |
其實,,縱觀李昌奎案整個輿情演變過程,不難發(fā)現(xiàn)該案引起輿論持續(xù)關(guān)注的“奧秘”:
一是從一開始,,該案就被置于與剛剛平息的藥家鑫案對比的平臺上,。7月4日較早的一篇時評就將兩案聯(lián)系起來,質(zhì)疑“比藥家鑫更兇殘為何不判死刑”,,隨后“賽家鑫”的標(biāo)簽更是預(yù)設(shè)了該案的輿情態(tài)勢,。
二是該案與以往不同,除了普通民眾表示出強烈的質(zhì)疑之外,,法學(xué)界也出現(xiàn)一片反對之聲,,包括法學(xué)教授,、律師以及法官等在內(nèi)的專業(yè)人士,紛紛從司法的法律適用上提出“少殺,、慎殺不等于不殺”等立論。
三是云南高院對于改判的理由和對輿論的回應(yīng)沒有說服力,,并未向公眾展現(xiàn)司法裁判的內(nèi)在邏輯,。
在普通網(wǎng)民,、意見領(lǐng)袖與法學(xué)專家如此罕見地具有一致立場的情境下,,法院面對的是“四面楚歌”,,壓力可想而知,。我想正是這樣的超強壓力,,讓法院在對自身改判的“正確性”堅持一段時間后,,不得不決定啟動再審程序,,而這很大程度上也預(yù)決了最終的司法結(jié)果,,如果法院不想再度招惹輿論質(zhì)疑,,那么該案的結(jié)論可能只有一個:判處李昌奎死刑立即執(zhí)行,。
在中國的現(xiàn)實語境中,,身處輿論漩渦中的司法很容易被置于和“民意”對立的立場,,最終則總是以司法屈從“民意”而化解。云南高院自然也不例外,,但其與“民意”抗?fàn)幍募ち页潭龋且酝痉C關(guān)所罕見的,。正因為如此,,法院行為背后的目的與動機,,就值得深究,。
法院何苦非要為一個沒有特權(quán)的普通犯罪人而得罪輿論呢,?這很可能與法院所追求的司法人文主義有關(guān),。
對于輿論的強烈反應(yīng),,云南高院應(yīng)該不會不清楚可能招致的后果,,尤其是在網(wǎng)絡(luò)上對西安藥家鑫案“殺聲震天”之后,緣何云南高院還敢“冒天下之大不韙”選擇與“民意”抗?fàn)幠兀?BR> 曾有人懷疑云南省高院在此案中徇私舞弊,,不過最終被輿論否決。在我看來,,或許正是李昌奎所具有了這種“一貧如洗”、幾乎沒有任何“司法腐敗空間”的背景,,才讓云南高院具有了與以往一些司法機關(guān)所不一樣的與“民意”對抗的“底氣”,。
法院又何苦非要為一個沒有特權(quán)的普通犯罪人而得罪輿論呢?筆者分析認(rèn)為,,這很可能與法院所追求的某種價值觀念有關(guān),。
如果司法者信奉的是司法人文主義,是貝卡利亞式的國家刑罰觀,,并具有推動社會法治觀念進步的理想,,那么對于死刑盡量少地適用甚至干脆不予適用,則是順理成章,、合乎邏輯的,。在有些國家,雖然法律上并未廢除死刑,,但司法實踐中幾乎不判死刑,。
這樣的揣測或許有些主觀,但還是能夠從下述事實中得到進一步印證:
一是云南高院在回應(yīng)中極力援引“寬嚴(yán)相濟”,、“少殺慎殺”的刑事政策,,尤其是7月13日,云南高院副院長田成有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“絕不能以一種公眾狂歡式的方法來判處一個人死刑,,這是對法律的玷污”,,殺人償命的陳舊觀點也要改改了,,“我們現(xiàn)在頂了這么大的壓力,但這個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個標(biāo)桿,、一個典型”,。
二是7月14日《南方周末》刊登的“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一位不愿署名的法官”文章,明確提出:現(xiàn)代文明社會里,,我們應(yīng)當(dāng)消除對死刑的迷信和崇拜,,不能再把死刑當(dāng)作是治理犯罪的靈丹妙藥。很顯然,,這并非一篇普通的文章,,而是帶有反映云南高院刑罰觀、死刑觀的文章,。
三是新近爆出的“賽銳”,,同樣兇殘的殺人手段,同樣被昭通中院一審判處死刑而二審改判死緩,。這是否可以說明:云南高院改判死緩并非一時的心血來潮,,最起碼在云南司法系統(tǒng)所管轄的地域,死緩的適用是有一個比較統(tǒng)一的“標(biāo)準(zhǔn)”或某種“普遍性原則”呢,?
在當(dāng)前民眾觀念,、司法體制的條件下,個別地方法院如果想要做一些有益于法治進步的超前事情,,便很容易陷入困境,。
遺憾的是,云南高院對于死緩的理解與適用,,并未顧及當(dāng)下中國的社會心理,。他們站在十年后的高度改判此案,出于法治觀念進步的立場與“民意”硬碰硬,,最終陷于“困獸之斗”的境地,。
應(yīng)當(dāng)說,法院選擇李昌奎案為突破口,,排除了藥家鑫案中的富二代,、官二代、大學(xué)生等敏感符號,,但這番觀念上的追求并未在程序上作出嚴(yán)密的設(shè)計,,使得貿(mào)然改判不僅沒有改變?nèi)藗儗τ谒佬虉髴?yīng)觀的迷戀,反而進一步鞏固了民眾傳統(tǒng)的死刑觀,,其結(jié)果或許是云南高院當(dāng)初始料未及的,。
對于改判所可能激起民意的劇烈反彈,云南省高院似乎防備不足,其中最為值得汲取教訓(xùn)的就是,,法官對于判決本身缺乏細(xì)致耐心的說理,。一再強調(diào)司法觀念上的宏觀考量,而忽視普通民眾對個案事實的微觀圍觀,,使得法院在引導(dǎo)民眾改變觀念的時候出現(xiàn)失效,,司法與輿論出現(xiàn)溝通上的“鴻溝“。演變到最后,,法院不得不選擇低調(diào)“認(rèn)錯”而終結(jié)這場輿情紛爭,,中國邁向廢除死刑進程中的又一個案例失敗了。
這樣的失敗其實有著更為深厚的體制背景,。在我國,,司法向來缺乏一種創(chuàng)造性的膽識和經(jīng)驗,尤其是地方法院,,既處于整個司法系統(tǒng)的嚴(yán)格管控之下,,又深陷入地方政治體制格局,其一般只能按部就班地適用法律,,在觸及各種底線的“主觀能動性的發(fā)揮”上經(jīng)驗不足,。對于中國目前的國民而言,死刑的撼動就會觸及到他們的心理底線,,而只要民眾“不答應(yīng)”,,別說是地方司法機關(guān),就是最高司法當(dāng)局乃至立法機關(guān),,都不敢妄動,。
這種背景下,個別地方法院如果想要做一些有益于法治進步的超前事情,,便很容易陷入困境,,甚至招致濫用司法自由裁量權(quán)的批評,。我們知道,,中國死刑包括死刑立即執(zhí)行和死刑緩期執(zhí)行,二者對于被告人雖有天壤之別,,但法律上關(guān)于“自首與減刑”以及“死刑與死緩”的差別界定并無清晰明確的標(biāo)準(zhǔn)區(qū)分,,法官手中的筆是向左還是向右,原本就有“生死判官”的意味,。如此,,對于一些惡性較大的犯罪分子究竟適用死刑還是死緩,勢必引發(fā)民眾的爭論和不滿,。在這種情況下,,法院違背公眾感受而做出超前性的司法判決,便很難獲得人們的理解,也難以獲得上級司法機關(guān)的支持,。
缺乏足夠的上層支持,,違背普通民眾的心理意愿,再良好的司法追求也可能會傷害到自身的司法權(quán)威,。
不難看出,,缺乏足夠的上層支持,違背普通民眾的心理意愿,,再良好的司法追求也可能會傷害到自身的司法權(quán)威,。無論是藥家鑫案還是李昌奎案,我們都未見到司法引導(dǎo)民意的權(quán)威增長,,相反是一種民意引導(dǎo)司法的趨勢擴張,。
在一國的法治大廈中,司法原本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,。杰斐遜說過,,(司法)“政府的這一分支將擔(dān)負(fù)處理沖突的重任,因為他們是理性最后的上訴地點,�,!币虼恕坝靡磺惺侄危顾痉C關(guān)受到尊重”,,讓司法享有至高的榮譽,,是維系法治的重要任務(wù)。遺憾的是,,經(jīng)由個案呈現(xiàn)出來的司法與民意的關(guān)系,,整體上乃是司法權(quán)威拜倒在民意之下的態(tài)勢。
為什么中國的民意總是傾向于影響司法決斷,?為何我們產(chǎn)生不了那種捍衛(wèi)司法權(quán)威的良性社會環(huán)境,?我感到這首先要歸因于司法機關(guān)自身的專業(yè)理性不足。司法需要保持理性,,這種理性包括克制,、謙抑,本質(zhì)上要求遵循司法內(nèi)在規(guī)律,,提高判決的邏輯分析能力,。如果有足夠的邏輯支撐,有充分的法律根據(jù),,那么我倒是很期待哪一天司法即便面臨再強的輿論質(zhì)疑也能從容堅守,,巋然不動地捍衛(wèi)自身理性。
與此同時,,普通民眾尤其是網(wǎng)民,,也需要尋求公民理性。網(wǎng)絡(luò)激發(fā)了公民的表達(dá)欲,但也帶來理性暫時性遺忘的廣場效應(yīng),。即便是再理性的人,,當(dāng)他置身于自己喜愛的足球賽場,也可能做出事后連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沖動言行,。這種沖動,,很可能對專業(yè)判斷的司法帶來片面性認(rèn)知,并在此基礎(chǔ)上形成消解司法權(quán)威的輿論狂潮,。因此,,培育網(wǎng)民的公民理性,學(xué)會獨立判斷,、自主言說的公民環(huán)境,,乃是我們從“激情歲月”邁向“法治生活”的必經(jīng)過程。
總之,,當(dāng)下不斷爆發(fā)的影響性個案,,呈現(xiàn)出來的司法與民意的鴻溝與隔膜,需要用理性來打通,,理性是二者形成共識的基礎(chǔ),。只有尋求到基于知識、理性之上的共識,,才能形成支撐法治社會的司法權(quán)威,,由此才能最終保護好每個公民的權(quán)利與自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