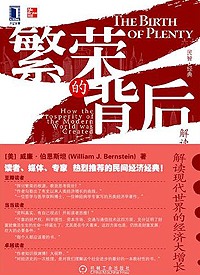 |
作者:(美)威廉·伯恩斯坦
出版社:機械工業(yè)出版社 |
威廉·伯恩斯坦是一名精神病從業(yè)醫(yī)師,,擁有化學和醫(yī)學兩個博士頭銜,,經濟學只是其業(yè)余愛好,。在經濟學領域著書立說,也是威廉·伯恩斯坦退休之后玩票所為,。孰料這一玩可不得了,,他連續(xù)出版多本備受歡迎的金融理論、資產組合投資,、貿易史著作,,“頭銜”也變成了“金融理論家”,或者不蹩腳的經濟學家,,遠比枯坐學院固守教條的同行靠譜,。
這本《繁榮的背后:解讀現代世界的經濟大增長》,旨在解答19世紀早期出現的引發(fā)現代經濟爆發(fā)式增長,,以及這種增長只出現在一些國家,,在另一些國家增長態(tài)勢不明顯甚至與增長潮流絕緣的原因。威廉·伯恩斯坦對此設問給出的回答是,,持續(xù),、無法逆轉的經濟增長需要具備四種制度條件:財產權、科學理性主義,、現代資本市場,、交通與通信技術。他首先分析19世紀之前若干個曾經短期繁榮的國家,、文明,,指出上述四種制度條件中一個或多個缺失,造成了這些國家和文明衰落,,并且,,缺失多個制度條件的后果要比只存在一個“短板”嚴重。
接下來,,威廉·伯恩斯坦分別就財產權等四種制度條件對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性,、不可或缺性進行了闡述,也同時論證了單有其中一項,,國家也無法實現長久的經濟繁榮,。值得稱道的是,有別于許多原教旨主義經濟學家,,威廉·伯恩斯坦在闡述資本(市場)一章中,,提到了近代荷蘭因過度沉溺于金融業(yè)務導致了衰落。荷蘭在17,、18世紀,,其國內發(fā)達的資本市場率先推出了海事保險、退休金、年金,、期貨,、期權、跨國證券上市以及共同基金等金融創(chuàng)新,,還涌現出真正意義的現代投資銀行,。在荷蘭,貸款的風險有史以來第一次可以打包出售,,并以不同名目的債券形式分攤給數以千計的投資者,由此推動了利息率(資金成本)的降低,,讓荷蘭資本家,、投機客踴躍融資在海內外投資。據統(tǒng)計,,荷蘭1800年的對外投資高達15
億荷蘭盾,,是荷蘭GDP的兩倍,這個比例遠遠高于現代的金融投資大國美國,,后者對外投資不到GDP的一半,。金融如此發(fā)達,金融獲利如此輕而易舉,,當時的荷蘭政府和資本家沒有動力完善監(jiān)管體系,,也缺乏風險判斷,大量外部債權均落得違約結局,,更關鍵的是,,這個國家的初期繁榮并不依靠技術進步這一現代財富的偉大發(fā)動機,因而不可避免的衰落,。
近現代英國是首個同時具備威廉·伯恩斯坦所說四種制度條件的國家,。英國對財產權的尊重,是這個國家自中世紀時代留下的政治遺產,,以《大憲章》的形式限制了王權,,遏制了幾百年里多位國王試圖擴權越界的努力。也正是因為王室權威相對衰弱,,近現代英國更能寬容技術創(chuàng)新,,除了工業(yè)革命前那些在各行業(yè)各領域起到重要奠基作用的發(fā)明創(chuàng)造外,這個國家還第一個系統(tǒng)地將科學方法應用于農業(yè),。英國“光榮革命”不僅從荷蘭引進了新國王威廉,,還引入了大批荷蘭及歐洲其他國家的金融家族,并一步步規(guī)范本國的資本市場,。等到蒸汽機等一連串實現交通與通信條件升級的新技術成果出現,,可以說,19世紀早期的英國在全球擁有了起跑優(yōu)勢。對照荷蘭與英國,,同時期的法國,、西班牙和日本卻仍然面臨推動騰飛發(fā)展的制度障礙,因而發(fā)展得更慢,,并留下了延至現代的負面社會,、文化和政治遺產。
在筆者看來,,這本書的前兩部分較為清晰的回答了威廉·伯恩斯坦的前述設問,,有關財產權等四種制度條件的價值意義的分析也頗為到位。正如本書中文版推薦序作者,、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宇燕所指出的,,威廉·伯恩斯坦在這本書中并沒有提出原創(chuàng)性理論見解,而是高效簡潔的引述了多位經濟史,、貿易史,、金融理論專家的名作論點,以易于被讀者看懂理解的方式整合起來,,成為一部“有理論一句的非小說文字”,,“憑借已有磚瓦筑造出具有別具一格功能的房屋來”。
但需要指出的是,,恰恰也因為威廉·伯恩斯坦非正統(tǒng)經濟學家的身份,、全盤借用他人研究成果著述的特點,書的前兩部分仍然存在一些瑕疵,,譬如,,第二章談及美國財產權法治傳統(tǒng)中專利保護體系時,作者忽略了或選擇性放棄的事實是:美國在20世紀前專利保護法律政策發(fā)明的對外歧視導向,,以最低成本引進來自歐洲的技術成果,;又如,將英國在近現代時期的崛起繁榮原因界定為四種制度條件的具備(甚至定論稱,,只要有了四種制度條件,,繁榮就會自然而然發(fā)生),無視當時作為日不落帝國的英國,,其發(fā)展從海外殖民地資源,、市場等獲得的非制度優(yōu)勢(英國20世紀損失了這些非制度優(yōu)勢,仍保留了前述四種制度條件,,也無法換回的衰落了),。
《繁榮的背后:解讀現代世界的經濟大增長》這本書更大的問題在第三部分——威廉·伯恩斯坦試圖將前述四種推動經濟繁榮出現的制度條件,進一步確定為充分必要條件(不需要其他因素),,甚至是有政治正確寓意的唯一模式——這個目標暫不論正確或者謬誤,,遠遠超出了依靠整合已有文獻著書立說的他的能力。書中第三部分也因此陷入顛三倒四的敘述,在發(fā)展,、幸福,、霸權等詞匯中艱難切換,在多處論述時將“財產權”直接置換為“法治”,。
作者有意論證財產權等四種條件之外,,學界重視的其他因素如民主只是經濟發(fā)展的成果,而不能成為進一步保證推動經濟持續(xù)發(fā)展和繁榮,,可能會起到相反作用,,舉出了當今世界許多民主政體國家陷入發(fā)展困境的案例,以及一些被稱為非民主政體的國家連續(xù)快速增長的情況,;甚至還暗示,,在保證財產權前提下實行必要專制的合理性。筆者認為,,威廉·伯恩斯坦的這種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解,本身是忽略民主發(fā)展完善程度,、民主與法治互相支撐,、缺失民主的經濟增長必然造成兩極分化進而葬送發(fā)展局面的惡性后果等一系列常識的誤判。